

长江经济带城际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系的边界效应及多维机制
|
韩明珑(1996—),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minglonghan1@163.com |
收稿日期: 2020-06-27
修回日期: 2020-11-2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471138)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706145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90007)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提升项目(YBNLTS2019-032)
Boundary Effect and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 of Inter-City Producer Services Network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ceived date: 2020-06-27
Revised date: 2020-11-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30
推动城市经济互动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之一。基于网络构建、模块度估计、变异系数(CV)等方法,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部分支企业数据识别长江经济带边界效应的空间特征,继而从多维边界效应、城市发展水平两大层面,构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联系的多维机制定量分析框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进行实证。研究发现: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依然存在顽固的边界效应,且在不同行业表现不同。②城市网络的分割发展特征是多维边界与城市发展水平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行政、政策、自然和文化等边界在其中发挥着强弱不等的阻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是与边界效应相抗衡的推动力。③不同服务业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韩明珑 , 何丹 , 高鹏 . 长江经济带城际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系的边界效应及多维机制[J]. 经济地理, 2021 , 41(3) : 126 -13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3.013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ity economic network is one of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modular estimation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this paper recogniz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undary effect of the YREB using the data of the headquarters branch of producer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ulti-dimensional boundary effect and urban development level,it construct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 of producer services network in the YREB and carries on empirical analysis by the means of th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ERGM).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ased on producer services,intercity connection still has stubborn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effect and present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gmentation of urban network are the result of multidimensional boundary barriers and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Administrative,policy,natur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play different degree of hindrance,urban development level is the driving force against the boundary effect. When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of urban network development is greater than the internal power,the boundary effect occurs. 3)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it exists difference in the intensity of boundary effects and the inner power of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vital to respec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dustry and conduct orderly integration guidance.
表1 ERGM模型变量选择Tab.1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ERGM |
| 变量名 | 内涵 | 示意 | 统计量 | 假设检验 |
|---|---|---|---|---|
| Edgecov | 网络协变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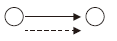 | 某种关系的存在影响城市经济联系网络 | |
| Nodecov | 点协变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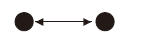 | 某属性强的城市是否更容易与其它城市发生联系 |
表2 边界指标、数据来源与说明Tab.2 Border indicators,data sources and explanations |
| 边界类型 | 边界名称 | 数据来源 | 网络构建 | 说明 |
|---|---|---|---|---|
| 行政边界 | 省际边界(X1) | 《中国行政区划图》 | 两城市跨越省份,记为1;同属一个省份,记为0 | 长江经济带包括9个省份,2个直辖市 |
| 政策边界 | 城市群边界(X2)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 两城市分别属于不同城市群,记为1;同属一个城市群,记为0 | 研究区内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其它地区3个大型城市群 |
| 自然边界 | 地形边界(X3) | 《中国地貌区划图》 | 两城市分别属于不同地貌区,记为1,同属一个地貌区,记为0 | 研究区主要包括6个主要地形地貌区 |
| 河流边界(X4) | 两城市处于长江不同侧,记为1,处于长江同侧,记为0 | 长江以北片区,长江以南片区 | ||
| 文化边界 | 方言边界(X5) |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 | 两城市所处不同方言片区,记为1,同属一个方言片区,记为0 | 研究区内主要包括湘语、赣语、徽语、吴语、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客家话和其它9个方言片区 |
| 民族边界(X6) | 《中国民族分布地图》 | 两城市分布的主要民族不同,记为1。同属一个民族区,记为0 | 研究区内主要分布有藏族、羌族、彝族等13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
表3 全行业ERGM结果Tab.3 ERGM results of the whole producer services |
| 基准模型 (模型1) | 多维边界变量 (模型2) | 综合模型 (模型3) | ||
|---|---|---|---|---|
| Edgecov省际边界 | X1 | -1.52*** | -0.09* | -1.03*** |
| Edgecov城市群边界 | X2 | -1.07*** | -0.93*** | |
| Edgecov地形边界 | X3 | -1.51*** | -1.22*** | |
| Edgecov河流边界 | X4 | 0.12** | -0.06* | |
| Edgecov方言边界 | X5 | -0.62*** | -0.91*** | |
| Edgecov民族边界 | X6 | -1.33*** | -0.16** | |
| Nodecov经济发展水平 | X7 | 0.73*** | ||
| X8 | 2.41*** | |||
| Nodecov科技教育水平 | X9 | 1.18*** | ||
| X10 | 0.09* | |||
| Nodecov信息化水平 | X11 | 1.11*** | ||
| X12 | 0.40*** | |||
| Edgecov距离网络 | X13 | 0.81*** | 1.08*** | 1.04*** |
| AIC | -14 610 | -16 729 | -21 843 | |
| BIC | -14 589 | -16 673 | -21 745 |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表4 分行业ERGM结果Tab.4 ERGM results of various producer services |
| 基准模型1 | 综合模型1 | 基准模型2 | 综合模型2 | 基准模型3 | 综合模型3 | ||
|---|---|---|---|---|---|---|---|
| Edgecov省际边界 | X1 | -1.00*** | -1.23*** | -1.40*** | -0.75*** | -1.42*** | -0.86*** |
| Edgecov城市群边界 | X2 | 0.11 | -1.04*** | -1.13*** | |||
| Edgecov地形边界 | X3 | -1.12** | -1.52*** | -1.20*** | |||
| Edgecov河流边界 | X4 | -0.04 | -0.07* | -0.14* | |||
| Edgecov方言边界 | X5 | -0.40*** | -0.70*** | -0.92*** | |||
| Edgecov民族边界 | X6 | 0.24* | -0.17** | -0.05** | |||
| Nodecov经济发展水平 | X7 | 2.62*** | 0.89*** | 0.99*** | |||
| X8 | 0.49*** | 2.13*** | 2.84*** | ||||
| Nodecov科技教育水平 | X9 | 1.00** | 1.16*** | 1.35*** | |||
| X10 | 0.36* | 0.06* | 0.42*** | ||||
| Nodecov信息化水平 | X11 | -0.30* | 1.18*** | 0.91*** | |||
| X12 | -0.22** | 0.41*** | 0.16** | ||||
| Edgecov距离网络 | X13 | 0.81*** | -0.46*** | 0.84*** | 1.07*** | 1.12*** | 1.07*** |
| AIC | -15 088 | -15 248 | -12 855 | -16 945 | 14 415 | -16 512 | |
| BIC | -15 067 | -15 150 | -13 057 | -16 847 | 14 359 | -16 414 |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 [1] |
王聪, 曹有挥, 宋伟轩, 等.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构建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7):1051-1059.
|
| [2] |
王聪, 曹有挥.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演化模式与机制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2):115-123.
|
| [3] |
夏骥. 市场分割与边界效应研究述评[J]. 区域经济评论, 2014(2):148-155.
|
| [4] |
|
| [5] |
|
| [6] |
王成龙, 刘慧, 张梦天. 边界效应研究进展及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9):1109-1118.
|
| [7] |
高鹏, 何丹, 宁越敏,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社团结构演化及其邻近机制——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网络分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4):578-586.
|
| [8] |
|
| [9] |
|
| [10] |
何丹, 单冲, 张盼盼, 等. 基于大学生认知地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认知[J]. 地理研究, 2018, 37(9):1818-1831.
|
| [11] |
魏后凯, 朱焕焕. 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界定与一体化推进策略[J]. 企业经济, 2015(9):12-18.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贺灿飞, 金璐璐, 刘颖. 多维邻近性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7, 36(9):15-28.
|
| [21] |
李琳, 韩宝龙. 地理与认知邻近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影响——以我国软件产业集群为典型案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1592-1605.
|
| [22] |
李郇, 徐现祥.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J]. 地理研究, 2006, 25(5):792-802.
|
| [23] |
许和连, 孙天阳, 成丽红. “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的指数随机图分析[J]. 财贸经济, 2015(12):74-88.
|
| [24] |
李天籽. 中国沿边的跨境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J]. 经济地理, 2015, 35(10):5-12.
|
| [25] |
余元春, 顾新, 陈一君. 跨区域技术转移边界效应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5):44-50.
|
| [26] |
宋周莺, 刘卫东, 刘毅. 中小企业集群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岭市鞋业集群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 26(4):121-129.
|
| [27] |
|
| [28] |
陈红霞.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4):128-135.
|
| [29] |
陈修颖. 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演化及重组[J]. 地理学报, 2007, 62(12):1265-1276.
|
| [30] |
|
| [31] |
|
| [32] |
刘华军, 杜广杰. 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研究[J]. 统计研究, 2018, 35(4):3-15.
|
| [33] |
申玉铭, 吴康, 任旺兵.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009, 28(6):1494-1507.
|
| [34] |
吕韬, 曹有挥, 陈雯, 等. 区域服务业时空演化的动力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8):1471-1482.
|
| [35] |
|
| [36] |
|
/
| 〈 |
|
〉 |